男女主角分别是荀子帝尧的其他类型小说《略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无删减+无广告》,由网络作家“动荡不安的红太郎”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统一观念只在统一的基督教会中得到部分的实现。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所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
《略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无删减+无广告》精彩片段
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统一观念只在统一的基督教会中得到部分的实现。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所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政治发展模式从分开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国虽然有过分裂,但统一却是主旋律。它的发展模式是从合开始而又复归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统一被视为常态,而分裂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是“乱”的表现。它必然要重归于“合”。
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国人执着于统一的心态在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对比。古代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区域或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腊人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内部的事务,不过不是为了使城邦强盛起来以承担统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像斯巴达那样以克敌致胜为目标,从而牺牲了公民优雅美善生活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所鄙视。城邦之间远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并土地和人民。在数百年间,城邦之间互相兼并的现象是十分少见的。
与此相反,春秋战国时代多国并立的现象从未被视为正常现象,而是
方向上各个国家的分裂,还有各国内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会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最终挣开了教会统一的纽带,从此以后,统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顽固的分立主义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就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城邦观念源于城邦属公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以及他们对自给自足理想的追求。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罗马城邦共和国便毁于自身的扩张。在希腊,类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达人就由于对被征服者的恐惧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国,由于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产业。“贵为天子者”,当“富有天下”。这是君的观念,也为臣所认同。由一家占有一国,由一国进而兼并“天下”,这是君主产业的扩大。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对它发生疑问。
先秦诸子(和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君主的“家臣”地位出发来认识政治问题的,所以,把“天下”统一于某一位君主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骄傲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正是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老子是个例外)。所以,大一统心态正是家臣心态的一个侧面。
无论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它们并非对国家的统一和扩张不感兴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标被置于这个目标之上。在希腊,是公民们对自己独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纪,是贵族们对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的维护,这些公民或贵族的集体,构成国家的中坚,任何外来势力企图奴役这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集团拼死的反抗。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维护城邦独立战争中失败而集体遭屠杀的事情。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反抗诺曼入侵中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的范围都是“天下”,统治者称“天子”。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人视野所及,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只把周边少量的“四夷”排除在外。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这是他们无可怀疑的目标。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这个“天下”就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历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尺地一民,尽入版藉”。宋太祖立国之初,于风雪之夜拜访重臣赵普,赵普问其缘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天下没有统一,竟会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灭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南唐国主李煜一再贬损自己,对宋恭顺称臣,可宋仍发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对宋太祖说:“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视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过这个话茬回答说:“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10结果使者无言以对。当使者再一次请求缓兵时,宋太祖却不耐烦再讲任何理由,“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有人在一边“安睡”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中国人在“天下”观的背景下对统一的强烈追求。
四、 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在大一统秩序下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天下”的情结。每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这张底板上构绘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蓝图。
希腊罗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这里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生长于这里的每一种文明都与周边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沟通。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周边众多民族之一,绝不敢把他们所居住
一、 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
从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理位置上说,它有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中心,由此辐射到周边地区。这个中心有时向其它方向有所偏移,但没有明显的错位。不像西方文明经历由希腊到罗马再到西欧的大幅度位移。它的边缘有时扩张,有时收缩,但总是在一个大体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区域内,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居住于其中心地带,而其它少数民族则分布于其边缘地区。这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域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政治实体,其家天下的政治性质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表现为单轨性,即王朝兴亡的单调地重复,家天下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千年不变。古人都知道,“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这的确是事实。君主专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唯一的、天然合理的、无可怀疑的政治体制。地理文化上的大一统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家天下。这在中国形成了万世不变的所谓“道统”。
中国古代文明生长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内。它的北边是无际无涯的荒漠和原始森林,西边为难以逾越的高原和高山所阻隔,东南是令人生畏的茫茫大海,这些自然障碍将古人与外界隔开,形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这与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世纪及近代大西洋文明的开放性地理环境形成鲜明对照。正是中国文明对外的相对隔绝,使它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内向性格,使中华民族有着一种独特内聚力。它使古代中国人在这些屏障以内,实现了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统一,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具有“墙文化”的特征,即对外封闭,内部则消除各种障碍而得到充分开放和贯通。
二、“合—分—合”的历史传统
中国有着其它民族少有的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是从统一开始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华夏或“天下”统一的共主或帝主。被人们不断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形成上古时代一
反常的、暂时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本来是一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纷纷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天下没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担号令诸侯之责,接着便是各国直接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种不断兼并扩张的驱动力,推动着各国不断地吞掉周边小国、弱国,最终走向各国的统一。这就是由春秋之初的所谓“八百诸侯”到战国时的“七雄”,最后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的历史过程。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种对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起的。诸子的学说都是出于对西周“一”的秩序瓦解的不安,他们纷纷提出的救世治国的方案,都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统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对统一的追求格外强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虽然也有过像公孙龙那样“离天下”的主张,那不过是一种与主流观念极不协调的怪论,他的主张是孤立的,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对待。正如荀子所说,所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
先秦诸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统一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情感,也奠定了后世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整个中国古代,大一统形成了政治传统和政治思想传统。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无可怀疑地维护统一。出现分裂时,就会激发出整合国家并使之归于统一的强烈冲动。得“一”则安,出现“分”、“多”、“乱”的情况则惶惶然。
三、 中国人的“天下”观
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阐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人的政治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协和万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罚则使“天下臣服”。禹的威势更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说,所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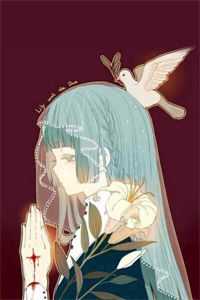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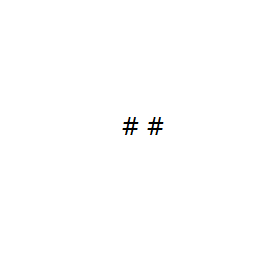
最新评论